苏晓梁骁是什么小说 苏晓梁骁全本免费阅读
苏晓梁骁是著名作者煮酒小诸葛成名小说作品中的主人翁,小说以形式来叙述,大大增加了难度。可想而知,作者对它倾注了多少心血!一睁眼从豪华别墅穿到漏雨的八十年代土坯房,苏晓看着油灯下年轻了四十岁的“奶奶”陷入沉默。刚想从空间掏出巧克力和牛肉干,却被隔壁拄拐退伍兵盯上:“你藏粮的本事,是敌特教的?”原以为要艰苦求生,她反手办起代销点,用现代营销卖断货。当厂长奶奶带着工人堵门讨货:“丫头,按你合同供货量,我们年底奖金就指你了!”后来成为女企业家的苏晓,看着电视里播报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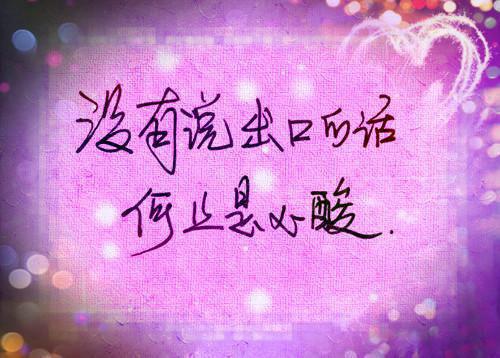
《带着别墅穿八零:养女竟是豪门骨》 第9章 免费试读
冰冷的空气像无数根细密的钢针,扎进苏晓因高烧而残留着潮红的皮肤里。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肋下的剧痛——那个在怀中深藏的硬角,如同烙在她肋骨上的刑具,冰冷的棱角隔着薄袄硌进单薄皮肉。从院子到灶间不过几步路,却走得她脊背僵硬,肩膀上的伤处火烧火燎地抽痛,每一次脚踩在冻硬的地面上都像踏在针毡。
灶房里的烟火气更浓了,混合着热腾腾的蒸腾水汽和烧干糊底的淡淡焦糊味,暖热的空气扑在脸上,却激得苏晓胃里一阵猛烈的翻搅,几乎要呕出来。
张菊香正背对着门口,弯腰在灶坑前,挥动着一柄旧火钳,噼里啪啦地拨弄着灶膛里燃烧不旺的柴火。劣质的柴草受潮难燃,浓烈的白烟卷着火舌倒灌出来,呛得她连声咳嗽,一边咳一边咒骂:“……烂屁股的瘟鸡,捡回来的这点柴火都湿透了!点火跟点死人的纸幡一样!咳咳……熏死老娘!”
她的注意力完全被灶膛里的顽固柴火吸引了,火光在她佝偻的背脊上跳动,拉长扭曲的影子。苏晓低垂着头,尽量缩小自己的存在感,身体僵硬地站在门边的阴影里,眼睛却死死盯着灶台案板的方向,心脏在胸腔里擂鼓般地撞击着肋骨下的硬角。
案板上,斜斜地靠着一把砍柴用的柴刀。刀身阔大,厚实沉重,是劈整根树墩子的家伙事。木柄油亮,刀口虽然有些钝了,但刃面在昏暗的光线下依旧泛着粗犷冰冷的青光。它离灶台有些距离,就杵在那里,像一个沉默冷硬的警示牌。
苏晓的目光黏在那把冰冷的凶器上,如同被磁石吸住。张菊香刚才在猪圈门口挥动它的暴戾身影和她此刻拨弄柴火的焦躁背影重叠,巨大的精神压力下,那沉甸甸的铁块竟让苏晓产生了一种诡异的安定感——仿佛只要它此刻不在张菊香手里挥舞,就是最大的安全。
张菊香终于把灶膛拨弄出点稳定的火势,直起腰,抹了一把被烟熏火燎出泪痕的脸,转身。一看到缩在门边阴影里、脸色惨白、眼神空洞地杵着的苏晓,新仇旧恨瞬间点燃。
“杵在那里装门神呐?!死相!”张菊香的声音像淬了毒的冰针,“一身泥的鬼样子还指望老娘给你饭吃?猪圈清了没?鸡喂了没?当自己是小姐太太?等着人伺候?!”
劈头盖脸的咒骂冰雹般砸下。苏晓的身体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怀里的硬角硌得更深。疼痛让她眼神更加瑟缩,下意识地抱紧了双臂,让那硬角深深嵌入肋下皮肉——仿佛只有这锥心的痛才能让她从这令人窒息的污言秽语里保持一丝清醒,才能死死压住那几乎冲破胸膛的牛肉干油污气味。
“扫……扫过了……”苏晓的声音嘶哑,像砂纸磨过木头,“猪……猪也喂了……”她艰难地试图解释,证明“价值”,声音却淹没在对方滔滔不绝的怒火里。
“呸!”一口浓痰带着热气狠狠砸在苏晓脚边灰黑的地面上。张菊香浑浊的眼睛因愤怒而圆瞪,“当老娘瞎?!看看你扫的猪圈!看看那圈底!糊弄鬼呢?!你当猪圈的粪是金子,舍不得铲走供着你?!还有那点猪食,猪嘴刚沾点皮就扫兴了!饿得直拱门!你是拿娘的老脸当抹布擦圈门去了?!……”
唾沫星子几乎喷到苏晓脸上。张菊香的手因为激动而颤抖着指向门外,那枯树枝一样的手指头差点戳到苏晓的鼻子。
“滚!给老娘滚出去打猪草!天黑前背不回满满一筐,你看老娘剁不剁了你的狗爪子塞灶膛里烧!”她骂得气喘吁吁,显然气急了,顺手就从旁边的柴火垛上抄起一根手臂粗、带着尖锐茬口的粗树枝,劈头盖脸地就朝苏晓头上砸来!“杵木头!滚!”
破空的风声带着绝望的怒意!
苏晓瞳孔骤缩!本能地想抱头蹲下躲开!
身体的剧痛和僵硬让她慢了半拍!
粗粝的树枝裹挟着柴草碎屑和尘土,狠狠地、结结实实地掴在她的肩颈相连的伤处!
“唔——!”苏晓闷哼一声!剧痛如同高压电流瞬间从肩窝窜遍全身!眼前猛的一黑!整个人被那股巨大的抽打力量带得踉跄着向后狠狠一栽!
“砰!”后背狠狠撞在冰冷的土门框上!
那一下撞击力量极大!后心抵着的门框棱角撞得她眼前金星乱迸!最致命的是怀中那个深藏的硬角——在这个角度、被外力强行挤压进躯体的瞬间,猛地向里一顶!狠狠钉在她左边下肋脆弱处的皮肉里!
尖锐的棱角甚至刺透了单薄的里衣!
噗!
一股尖锐到无法形容的剧痛从肋下猛冲上来!不是皮外伤的痛楚,而是内脏仿佛被一根冰锥狠狠刺穿的恐怖感觉!
苏晓只觉得喉头猛地一甜!一股带着浓烈铁锈味的液体毫无预兆地冲破牙关,汹涌地从嘴角溢出!温热、浓稠、带着身体的余热!
张菊香举着粗树枝还想再砸的手僵在半空,浑浊的瞳孔里倒映着苏晓后背抵着门框往下瘫滑、嘴角那抹刺目猩红的景象!
那点鲜红的血迹在昏暗、污秽的灶间光线里,突兀得如同雪地里的梅!
张菊香那滔天的怒气像是被瞬间冻结凝固了!脸上因愤怒而狰狞的表情僵硬在那里,只剩下茫然和一闪而过的、极其纯粹的惊惧!这血……真……真打出大毛病了?!那肩骨……真断了?
灶坑里,一根湿柴烧透了,里面蕴藏的水汽被烤干,发出一声极其短暂的、轻细的“啵”声,随即塌陷成灰烬的噗簌声。
这细微到几乎被忽略的声响,却在苏晓此刻被剧痛无限放大的感官中,如同在死寂深潭投入一颗石子!
“哇……”
一口滚烫的、带着浓重铁锈甜腥味的鲜红液体再次不受控制地从苏晓嘴角涌出,黏稠地淌过下巴,滴落在她紧紧抱着肋下的那只手背和破烂的袄子上。
她甚至能感觉到怀里的硬角纹丝不动,冰冷地深陷在痛觉神经最密集之处,像一个冰冷的恶魔在嘲弄——它找到了弱点!
苏晓的身体顺着冰冷的门框彻底瘫软下来,滑坐到冰冷的地面。她蜷缩着,头深深埋在屈起的膝盖和环抱着的手臂里,整个身体剧烈地抽搐颤抖,肩膀和肋下双重撕裂的剧痛像两条冰冷的毒蛇啃噬着神经。剧烈的咳嗽被死死压抑在喉咙深处,每一次压抑都加重了内腑的翻涌。额头滚烫,冷汗瞬间浸透了单薄的里衣。视野像被泼了红墨,阵阵发黑晕眩。
灶房里陷入一种诡异的死寂。只有灶膛里柴草燃烧偶尔发出的噼啪爆裂声。张菊香粗重的喘息僵在那里,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地上那团剧烈颤抖的身影和她手背上、袄子上那刺目的、蔓延开的暗红湿痕。握着粗树枝的手指关节泛着青白,微微发着抖。苏晓那压抑在喉咙深处、濒死般的细微抽气和呜咽,在这寂静里像一把钝锯子在磨人的神经。
时间像是黏稠的沥青,缓慢流动。
就在这压抑到极致的时刻——
院子外的方向,隔着低矮的篱笆墙,远远地传来一道略显苍老、带着某种程式化热情和熟练套路的吆喝声:“苏老哥!菊香嫂子!在家的吧?村东头老陈家二小子,捎个话!托供销社李会计的福!他家走丢那头黑伢猪,昨个夜里找着啦!就在东沟子那片烂洼地里!让别太着急上火!”
这声音像是投入冰面的石子!
张菊香被这突来的外部声浪惊得浑身一哆嗦!猛地从对“打坏”苏晓后果的惊惧和无所适从中惊醒!
她浑浊的眼睛飞快地转动了几下,脸色陡然变得更加难看!那头黑猪是她昨晚咒骂了半宿的由头!现在被点破找到了,让她满腔怨毒无处发泄的愤怒瞬间转了方向!更让她惊惧的是——那声音在院外!要是看到、或者听出点什么……
不行!绝不能让外人看到自家屋里死人!更不能再耽误!万一……万一这死丫头真死在屋里……
张菊香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丢开那根还在滴答污泥的粗树枝,几步冲到门口,一把拉开虚掩的院门缝隙,冲着声音来源、篱笆墙外的小道方向,用尽力气挤出一点佯装的热情:“哎!听见啦!多谢他李会计操心!谢你家跑腿儿嘞!……”声音拔得很高,带着虚张声势的尖利,试图盖过灶房里压抑的动静。
这声音让蜷缩在地、忍受着地狱般痛苦的苏晓,浑身剧颤了一下!眼角的泪和血混在一起,滴进泥尘里。她牙关咬得咯咯作响,用尽身体最后一丝力气,死命地将那个深陷肋下的冰冷硬角往肉里更深地挤压!仿佛只有这种以痛制痛的极端方式,才能让她在内外交煎的炼狱中保持一线清明,才能在张菊香即将爆发的后续风暴中找到唯一的“缝隙”!
她需要那个缝隙!一个可以暂时离开这炼狱般院子的喘息之机!
院外那人得了回应,也没进来细看,吆喝了一句“没事就好”,脚步声踢踢踏踏地走远了。
篱笆门被张菊香用力摔上,“哐当”一声响!她的脸瞬间扭曲回狰狞,猛地转身踏进灶房!看着地上瘫成一团、如同被抽掉脊梁骨的苏晓,尤其是她手背和衣襟上再次晕开的新鲜血迹,那点子惊惧被无边的厌烦和“麻烦要砸手里”的恐慌彻底取代!
“没用的瘟鸡!还死狗一样躺着挺尸?!”张菊香几步上前,粗糙的手指因为怒气和某种潜在的发虚,指着苏晓的鼻子咒骂,唾沫飞溅,“吐两口血就装死狗了?!老娘告诉你!今儿没打够五捆干柴回来给老娘烧炕,你就死在野地里也别回来了!”声音尖利到变调,“烂骨头了?那就爬出去!爬着去打柴!”
这歇斯底里的咆哮,每一个字都像带着倒刺的鞭子抽在苏晓紧缩的灵魂上。但其中那句“爬出去”、“死在野地里也别回来了”,却像绝望地狱里透出的一丝缝隙!
苏晓埋在臂弯里的脸抬起一点,沾满血泪污泥的头发下,那双刚刚还因剧痛而涣散的眼睛里,猛地燃起一簇惊人的亮光!那亮光带着孤注一掷的癫狂!
一个在死亡边缘被挤榨出来的念头,狠狠撞进脑海!
村东头老陈家……
那个喊话的方向……
那里……
有……村医?
一个极其模糊、带着强烈渴求的名字像水草一样浮上被剧痛覆盖的记忆碎片——老陈瞎子!
一个常年背着破木箱、装着劣质药面草药针头、在十里八村给人看头疼脑热、接骨扎针的老村医!一个……可能看病便宜、也容易被糊弄过去的……郎中?!
相关Tags:最大









